2002级 教育科学学院 王波
2022年,江苏师范大学将迎来70华诞。遥想2002年,我第二次高考考进了江苏师大的前身,当时的徐州师范大学。在此前一年,作为当地高中的文科第一名,凭借高出江苏省一本线40多分的成绩,我还憧憬着在大城市的所谓名牌大学,开启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一直等到八月底,连周围报考大专的同学都被录取了,我却没有收到任何大学的通知书。当时家里还没装电话,跑到几公里外的大舅家电话查询录取情况,无果。我脑子一阵发蒙,浑身颤抖。回家途中,为让舅舅放心而挤出的苦笑还僵在脸上,忽然间风雨交加,天昏地暗。我两眼发直,毫无感觉,任凭雨水打在脸上,浇透全身,泪水夺眶而出。风雨如晦,前路渺渺;乡间窄路,泥泞难行。直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瘦小身影,那是我的母亲,撑着一把破伞来接她不争气的儿子了。我抹一把脸,压住哭腔说,“妈妈,估计要去复读了”。我妈则说,“再考一次就是,以后做个乡村教师就很了不起啦,农忙了还能帮我割麦插秧。”我知道这是给我宽心的话,其实她心里比谁都难过。后来在县中复读的时候,一位同学在作文里写道,他母亲说就算捡破烂也会供他上大学。于是这位同学就梦到在小城昏暗的路灯下,自己的妈妈背着口袋,抓着钩子,在垃圾堆旁这里翻翻,那里刨刨。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这篇作文,就听见复读班的不少同学趴在课桌上抽泣。
实际上,我们都不想留在江苏复读。因为江苏的高考政策频繁改革,第二年就要改考文理大综合了。而我们都或者是文科生,或者是理科生。只有一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及时把缺了三年的课补上来?听说隔壁山东省仍然文理分科,我就请小舅开着他突突作响的柴油车,把我送到运河边,过湖去看看。坐了一小时的轮渡,又转乘一小时的汽车,我只身找到了当地一中的一位主任。他得知我的分数,很热情地邀请我入校复读,甚至答应给一笔奖学金。听说黑龙江省也是文理分科,我又连夜跟父亲骑了很久的车,去表哥家问能否去黑龙江。在尚未满18岁的我的心中,这或许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四处抱怨命运者,戚戚于失。而只要有一线机会,就要去争取。我的几乎每一位同学,都明白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还在高二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们的老师都跑光了。南方的高收入挖走了我们的老师。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多数同学仍然能坚持自学。所以高四期间,尽管我是那种被问到7X8等于几,就会晕倒在地上流鼻血的学生,然而还是强迫自己把丢了两年的物理、化学、生物捡了起来。当其他同学在家人陪伴下兴高采烈去大学报到之时,我却不得不独自面对完全陌生的巨大挑战,从基本的牛顿三大定律、化合价和碱基互补配对重新开始,试图从蒙眼的命运女神手中,紧紧抓过那飘忽结局背后的隐秘之弦。
我似乎并没有赢得与命运女神的拔河比赛。虽然春天的模拟考试,我居然考出了清华北大的分数,被一直鼓励我、还让我当一百多人的班长的班主任特地找去促膝长谈,但是在真正高考的时候,面对全新文理综合卷的理科题目,第一题没把握,我皱眉;第二题没做完,我苦笑;第三题做不出,我释然。就这样吧,我当时想,能做的我都做了。当时发小的姐姐在徐师大读书。考完大综合,我对他说,告诉你姐,我要跟她做校友了。所以我一直非常感激母校,在我飘零无依之时,是母校收留了我,给了我宝贵的读书机会!高四这一年让我知道,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纵然能够欣赏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或者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这两门课程的做题家。这两部书,还有其他的很多书,是这一时期的另一收获。当时我买了非常多的古旧书籍,为了省出买书钱,经常不吃饭。后来和书店老板熟了,他就会在进货时把我喜欢的书单独留出来。印象深刻的是以一元一本的价格,入手《读书》从创刊直到新世纪的几乎每一期杂志。这一爱好在读大学的时候进一步发荣滋长。当时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周六上午去快哉亭附近的花鸟市场淘书。每每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乘着19路公交,黄昏时分在东门下车,到天一面馆点上一碗两块五的番茄鸡蛋面,就着一小碟花生米,边吃边读,“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如今再也吃不到那样的美味了。我的很多朋友也是通过买书认识的,比如晓俊,徐师大最出色的诗人。他在三食堂门口卖书,我下课路过买书。聊得太投机,我就打了饭邀他到宿舍边吃边谈。他把学费挪去添置乐器,自己组了个乐队,安顿在公寓附近租的顶楼毛坯房。月光如水,烛影摇曳,我和凌北、影子他们环坐四周,听他弹着吉他浅吟低唱: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拿着这把钥匙。
结婚吧,艾伦……”
回想起来,那几乎是一种超越性的、几乎和世俗无关的境界。母校真的为我们撑起了一座超绝尘寰的象牙之塔。我素描过逶迤的后山,漫溯山下清冽的小河,倚暖河边石栏上的青苔,体会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学识渊博的各位老师,朝气蓬勃的同学们,充箱盈架的敬文图书馆,丰富多彩的讲座,则让我理解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当时的班主任陈老师特别关爱学生,除了尽心竭力教统计学,在班会时总教导要锤炼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他常把我们叫到家里做客,而美丽的师母熊老师恰好教我们教育学。她会备好水果,笑着看陈老师与我们谈天。贾老师学术功力深厚,原泉混混,每次上课都好像在给我们灌顶加持。他知道我对哲学感兴趣,就把自己用过的刘放桐先生《现代西方哲学》给我看。泛黄的书页上,密密匝匝的小楷,写满了贾老师的读书心得。教我们实验心理学的欧阳老师看起来文静优雅,却干练干脆,雄而有侠气。美丽热情的李老师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她的团体咨询课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只要几个简单易行的小游戏,就能神奇地调动活跃团体的气氛。母校的老师们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他们和校园里胸怀蓝天、深植沃土的法桐水杉一起,为我们遮挡了外面的万丈红尘。这样的身体力行,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后来许倬云先生教我的,“我们读书人读书不是为学位,不是为地位。读书是为生命,读书是为自己求心之所安”。
同学们也是互敬互爱,到现在我们彼此之间仍常来常往,倍感亲切。我还记得有一次晚自习,跟几位同学骑车十几公里到市区,帮人去贴家教广告,挣一点生活费。通过这种途径,以及更多匪夷所思的其他方式,加上学校给予的奖学金,我挣到了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深夜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路边吃烧烤。那初夏之夜的烤肉香味,仿佛至今仍萦绕鼻间。烧烤摊上袅袅升起的青色烟雾,宛如此刻恍然自失的回忆。那个时候,我活得真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吉普赛人。受命主编学院的杂志不说,还兴致勃勃要去组建自己的社团。我央请美院的奕君学姐设计杂志封面,特地嘱咐她要突出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又要体现我们杂志的厚重高端大气。最后我俩选了一头大象。那是化用达利的《胜利之象》,长着夸张长腿的高耸入云的巨型动物,仿佛王小波笔下的李靖,踩着高跷疾步如飞地走过纵横交错的彭城街道。
我花时间最多的地方,还是敬文图书馆。图书馆有四层楼,大学四年,我从第一层读到第四层,尤其是特藏室书籍上的灰尘,时常让人喷嚏不断。那时候复印机尚未十分普及,我就一页一页地抄书,往往直到闭馆音乐响起,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在那做梦的年纪,那个少年也曾幻想透过某个书架,“从某部小说的书页中找到生活,命中注定的女主人公,对他屈尊微笑”。
是母校的老师们带着我第一次踏进心理学的神秘大门。“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也许是个人气质的原因,不擅长计算的我原以为会在这里发现关于最为广阔的人的心灵的奥秘。但是在当时那个尚未更事的年轻人眼里,他最终遭遇的似乎却是冰冷的仪器、枯燥的数字、繁琐的方法、抽象的概念和机械的范畴。草地上开满鲜花,我们却只被允许报告饲料。又是在老师们宽容的引导下,我投入到对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心理学的阅读中。先是尝试让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对话,发表了第一篇所谓CSSCI论文,继而试图寻找心理咨询的解释学基础,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同时用幼稚的诗歌反对所谓“变态心理学”:“梵高迸裂的脑袋后面最热烈的血色向日葵……潘帕斯草原的萨满焚起艾香,探险家在法老的咒语中死去。城市的金属思念故乡的矿苗,鳞次栉比的大厦是文明的白骨……穿过庄严夜晚的黑暗门柱,追溯英雄消逝的冥想家园”。可以说,当时这种对传统心理学的不满,基本是出于一种不着调的人本主义热情。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仅仅诉诸单纯的热情是贫乏和肤浅的。它不足以内在地切入传统心理学的要害之处,以促使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有所改变。
所以,我永远忘不了2004年冬天经历的那次思想冲撞。寒假之前的一个庸常午后,我又一次走进敬文图书馆,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紫色封皮的书,倚靠在窗边热烘烘的暖气片上读了起来。才翻阅几页,已被暖气烤得慵懒的精神就立刻为之一振。我忍不住暗暗惊呼,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原来还可以这样写作!那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是如此浓重和凝缩,以至于当时每看一段,几乎都要先深吸一口气,继而屏气凝神,沉潜品味,然后再抬起头,气息长舒,呆望远方,恍然自失。此时窗外彤云密布,朔风紧起,纷纷暮雪,有碎玉声。北国的第一场冬雪自高天飘然洒落。是的,阅读这样的书,需要适应高处寒冷的空气、适应一切意义上的严冬跋涉、天寒地冻和高山峻岭。“需要登上高山之巅,扫尽一切云雾和混沌,只听到万物的真实声音,粗犷而严峻,但字字清晰可懂!”(尼采语)这本书的名字是《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凡能吸入如此作品气息的人就知道,这是来自高原的风,是沁人心脾的空气。呼吸它的人需要天赋的体魄,否则就会有受寒的危险。“如今你苍白而立,命定迟游于冬季,恰似轻烟一缕,总将寒冷天穹找寻”。寒冰在近、孤寂无边,但万物在光明的笼罩下多么宁静!
韦伯说,人的天职就是履行一种呼召(calling),“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而“灵感在科学中起到的作用毫不逊于它在艺术中的作用”。那一刻,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天职呼召和学术灵感。“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生或许就是这种在层层限制中层层超越的天命传承?两次高考留下的创伤,最开始是母校抚慰的;至今依然梦见的青春岁月,起初是在母校遭逢的;后来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是从母校迈出的。所以,我感恩母校!
作者简介:
王波,男,汉族,江苏徐州人,2002年9月-2006年6月就读于我校教育科学学院学校心理教育专业。后获得南京大学哲学系与约克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毕业后放弃美国哲学心理学博士全额奖学金留校任教,先后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副教授、约克大学访问教授。后晋升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入选福建省高层次A类人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市杰出青年、厦门市高层次出国留学人才),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丛书”主编,另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四度荣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科研原创奖。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Theory & Psychology》《Culture & Psychology》《应用心理研究》(台湾地区)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并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专著由科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等出版。


在哥本哈根参会期间,于安徒生故居处留影

在匹兹堡大学访学期间,于Point State Park三河交汇处留影

受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教授Helen Longino邀请,赴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访学。此为访学期间与Longino教授合影

得国学大师许倬云先生亲炙,此为在许先生匹兹堡家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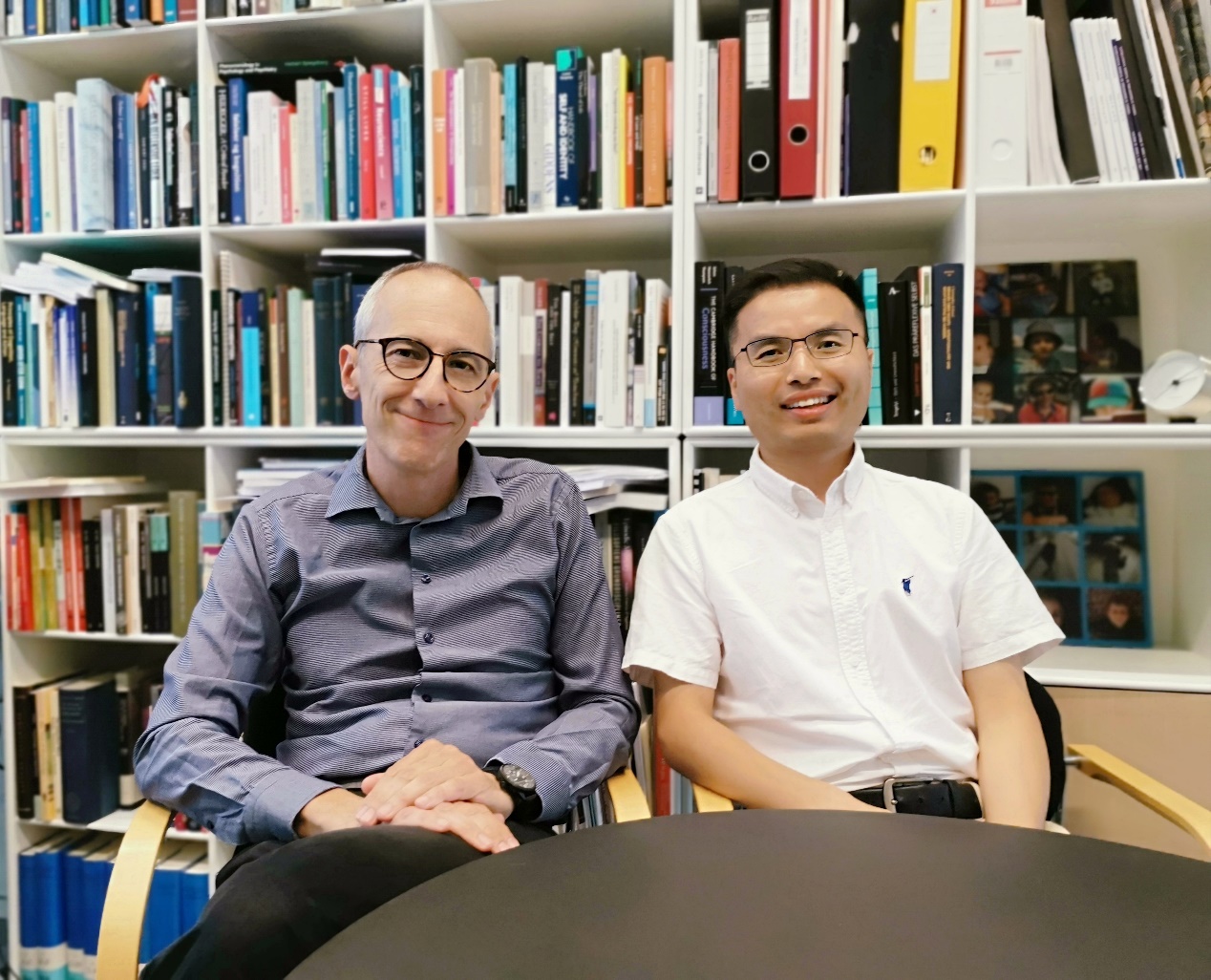
与国际著名哲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哲学系Dan Zahavi教授一番畅谈后(该文中译版发表于《世界哲学》),在其办公室合影

在约克大学访学期间,受邀赴女皇大学心理系参访,并与相识近20年的著名文化心理学家Floyd Rudmin教授合影留念



